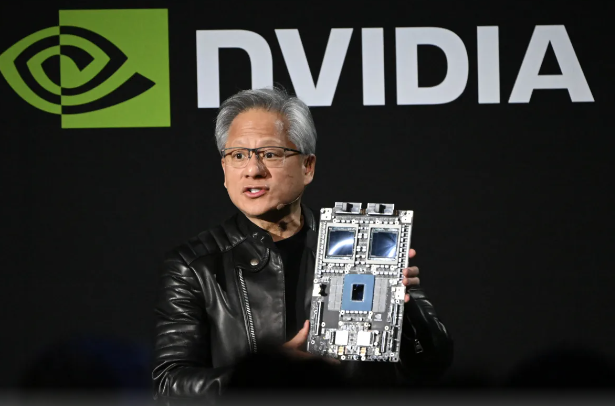种种迹象表明,中国的村镇化进程已经展开。
最显著的例子是乌镇之再度兴起。明清时代极为繁荣的乌镇,进入二十世纪后,伴随着沿海城市的兴起,缓慢衰落。尤其是到二十世纪中期,镇里工商业被人为取消,几乎丧失生机。但八十年代以后,农民在此发展工商业;九十年代以来,旅游业则迅速发展。由此,乌镇恢复活力。在此基础上,政府确立此处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,古老的乌镇一举成为最时兴的互联网产业小镇。
乌镇的例子不是个别的。目前,不少地方已仿照这一模式建设特色产业小镇。就在北京,政府已确定,在房山区长沟镇建设基金小镇。北京已患上严重的大城市病,政府积极筹划疏解各种非首都功能。其实,不少产业是可以外迁的,而以小镇模式外迁是一个选择,可保持产业之相对聚集。长沟这样村镇优美的环境,也确实可以吸引产业从业人员外迁。
如果说,这些特色产业小镇的兴起还有较强的政府背景,那么,另外一种小镇的兴起,则纯粹是技术和市场驱动的,此即淘宝村、镇。
第三届淘宝村大会刚闭幕,据阿里研究院最新发布的《2015年淘宝村报告》,截至目前,全国涌现出淘宝村780个,淘宝镇71个。笔者前不久与一批学者参访江苏曹县大集镇和江苏睢宁沙集镇,所见所闻,同行者无不讶异、惊喜:一大批企业,在相对贫穷、也无资源优势的两地,借助互联网搭建的交易网络得以迅速成长。
与本文讨论问题相关的是,这里曾出外打工、上学、经商的人口又在回流,这些地方的官员已经在认真地思考就地城镇化的问题。
如果我们相信互联网重塑经济社会秩序的力量,那就不能不认真地思考,人口大规模集中之城市化是经济社会演进的必然规律么?村镇化是否可能,并且较好?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,这一点简直就是确凿无疑的。
实际上,这已是我们所见证的第二轮村镇化。
过去几十年,在鲜亮的城市化背后,其实一直有强劲的村镇化潜流。天则经济研究所专门对此现象进行过研究,我们注意到两类市镇:一类是八十年代兴起的工商业强镇,江浙、福建、广东等地,此类市镇甚多。另一类不那么显著,但也相当重要,即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兴起于大城市郊区的居住区,最著名者是京冀交界处的燕郊镇。
令人遗憾的是,囿于城市化理论,理论界对这一现象缺乏深入研究,决策者基本视而不见,这两类市镇始终局促于现有行政架构中,无法自由舒展,结果,其产业升级缓慢,社会文化秩序无法正常生长。尤其是后来,两者受到市、县城市化进程的挤压,今天,似已黯然失色。
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,面对正在兴起的第二轮村镇化趋势,学界和决策者应当有文化和理论之自觉,也即从文化和理论两个方面,深入认识中国城镇化之内在机理。
首先,从文化角度看,由儒家文化塑造出中国人的精神与中国以西诸族群有所不同,表现在经济社会生态上的区别主要在于:由于普遍的身份制,在中国以西,文明始终聚集于城市,乡村是野蛮的,无文明可言,工业化就发生于享有特权的城市;但在中国,身份制早就废除,人口、资源可自由流动,故城乡大体上是贯通的。
唐宋以来,这一点尤为明显。明清时代中国经济已深度卷入全球分工体系中,固然有若干城市高度发达,规模也较大,但始终不是城市一枝独秀,相反,大量工商业活动发生于村、镇,镇的作用是沟通村与城市,农村产品由此进入全球市场。由此,中国早期工业化不是造就若干大城市,而是造就大量工商业强镇,前面说到的乌镇就是这方面的典型。
之所以出现这种分散于村镇的工业化,根本原因是,人民自由,农民可不离村而从事工、商业;在儒家熏陶下,人民普遍有自主、自强精神,即便最普通的农民也相信,通过企业家式决断,自己可以改变境遇。而这种分散的工业化适应了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,其效益普遍惠及农民。
有人可能争论,这样的工业化-城镇化模式不利于发生工业革命,此说不能成立,但暂不讨论。二十世纪中期,中国政府确实接受了来自欧美的工业化-城镇化模式,以城、乡两分为前提,强制在城市-乡村建立空间上两分的产业分工体系,市民-农民成为两种身份。这样,工业化只在城市进行,由此确实推动了大工业化进程,政府建立了很多大工厂。在此背景下,乌镇之类传统市镇被人为取消了工商产业。
但是,这种工业化与农民广大人口无关,注定难以为继。从七十年代起,工业化重寻其动力,乃突破城乡分割藩篱,向农村迁移。由此开始中国第二轮工业化,这一次主要发生于村、镇。事实上,明清时代曾经繁荣的镇再度成为本轮工业化的重镇,上文所说的工商业强镇就此出现。这只是历史的一次回归。
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,政府积极推动城市化,集中资源发展县以上的建制市。主流的城市化-城镇化理论似乎也认定,未来中国绝大多数人口要住在城市,工商业活动只适合在城市发展,有些学者甚至主张,城市越大,越有效率。
这些学者常以自由市场的经济学立论,但其实,这正是毛时代工业化-城市化的理论依据。我们不能不从理论上认真思考,究竟什么是规模经济?
主张人口城市化、发展大城市的理论依据是规模经济,但“规模”可有两种意义:一种体现在物理意义上,人口、资源集中于城市,可称之为“硬规模”。另一种是“软规模”,也即,网络规模,以及由此聚集的企业家规模。
为说明这一点,再看看历史。明清时代,中国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,且效率极高,但其生产模式是,以家庭为单元之小微企业存活于庞大的商业交易网络中,后者提供丰富的资源选项,前者运用这些资源生产。这一模式效率极高,即便后来西方的大工厂也未必有能力与之竞争。原因在于,在其中活动的经济主体不是被动听从工厂主指挥的工人,而是具有创造精神之企业家。也即在此体系中,市场中的企业家比率(这是我生造的词,指各种市场主体中企业家所占之比例),远高于大工厂、大城市模式,而市场的生命力全在于企业家。
今天,互联网经济似乎给这种模式再度复兴提供了一次机遇。淘宝村、镇的基本运作模式正式,无数小微企业存活于架构在互联网的全球性商业网络中,农民在家中就卷入全球市场,不是作为只出力的工人,而是作为劳心又劳力的企业家,其效率焉能不高?另一方面,此网络以极低成本贯通城、镇、乡,再加上目前高度发达的物流业,基本上可以替代城市的“硬规模经济”。
至于为什么自古以来,在中国,就有人愿意维持这么一个网络,仍然需要回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探索。姜奇平先生在今年第十二期《读书》杂志发表文章,《三生万物:复杂共同体视角中的“互联网+中国”》,可供参考。
总之,互联网正在塑造经济社会秩序之雏形,让我们隐约看到了中国古老的经济社会秩序重生之可能,这两个趋势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,重新思考城市与乡村的关系、工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,重新思考中国究竟需要城市化、城镇化、还是村镇化,至于重新思考之关键,则在于历史的自觉、文化的自觉。